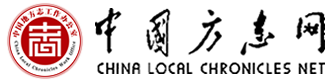方志的性质是什么?这是研究方志学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方志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基础。古往今来,历代学者一直对方志的性质孜孜探求不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以来,方志界围绕方志性质问题开展了规模空前的讨论,诸说纷纭,观点达几十种,如地理书、历史书、史地兼有之书、辅治之书、地方信息之书、综合性著作、历史性资料、地方百科全书、一方古今总览、科学文献、资料性著述等主张,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说明,学术界对方志性质的认识,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而随着修志实践的深入发展,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
归纳起来,关于方志性质,主要有如下观点。
一 “地理书”说
这种观点认为,方志源于《禹贡》、《山海经》等先秦地理著作,因这些著作是按照一定的行政区域,记载山川形势、风土人情、物产田赋和名胜古迹的,属于地理书。此观点约始于《隋书·经籍志》,汉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唐、宋、元代志书序跋中每有类似说法。如唐代颜师古即提出:“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互会,颇失其真。”在此,颜师古认为方志属于地理。刘知几亦称:“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宋代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司马光、欧阳忞、王象之等。元代,黄溍也持此论:“溍窃惟昔之言地理者,有图有志,图以知山川形势、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语言土俗、博古久远之事。”至清代,戴震、洪亮吉、谢启昆等认为“一方之志,沿革最要”,力主“志乘为地理专书”。
近现代一些学者(以地理学者居多)继承这一观点,仍视方志为地理书。民国时期,梁园东说:“中国之地方志,以今日视之,实为一种不完全的地理书。”台湾学者陶元珍也力主方志为地理书。他说:“章实斋以旷代史才,弗克与修国史,其致力方志,有同牛刀割鸡,以修史之道修志,究非所宜。在实斋大材小用,聊以消磨岁月,固出于不得已也!后之学者,弗明实斋微旨,于皮相发挥实斋所论,益为尽致,实斋本意,岂如是乎?地方不应有史,方志亦非国史之基。就现代趋势言,方志实应较重地理。戴东源当年之论,诚有可取之处。”他主张:“地质、地形、水文、土壤、气候诸项,均宜增列,以新地理之眼光述新方志,庶山水、物产两类诸项,均有其科学基础。”[1]
地方志属于地理学科的观点,也反映在目录学上。《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正史,梁阮孝绪《七录》、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郑樵《通志·艺文略》、明焦竑《国史·经籍志》、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民国《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及今人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王重民《中国善本书目提要》等历代公私书目,大多将方志列为地理之属,视方志为地理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把方志编入地理类。
方志之所以被视为地理书,据黄苇等著《方志学》分析,大致有三种原因:一是方志为一方之志,大至省、市、府志,中至州、厅、县志,小至乡镇志,都以特定区域为界线,记载这一界线内的建置沿革、风土民情、工农业生产等,有鲜明的地域性;二是每部志书都用大量篇幅,首先记载一地的地理内容;三是方志源于《禹贡》等先秦地理著作。
二 “历史书”说
这种观点认为方志是地方历史书,乃“史之流”、“史之属”。此观点较早可追溯至《周礼》。《周礼·春官·外史》提出:“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曰:“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方志编纂者,把方志看成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如宋代郑兴裔提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元代杨维桢、杨敬德、许汝霖,明代康海、严嵩、王世贞、张居正、李东阳、冯梦龙等,皆持方志为史论,视方志为“史之流”。如杨维桢在至正《昆山志序》中称:“金匮之编,一国之史也;图经,一郡之史也。”李东阳在嘉靖《许州志序》中提出:“大则史,小则志,兼行而互证也。”冯梦龙在《寿宁待志·旧志考误》中也提出“志书即一邑之史”的观点。清代章学诚是主张“志属史体”最有名的代表,他对于戴震的志属“地理说”曾予批评:“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有,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夫图事之要,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则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他认为志、史同源异流,志书乃史书的具体而微,志乃史裁、志属信史,方志乃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之全史。乾嘉间,施润章、李绂、纪昀等亦持类似观点。清末民国时期,梁启超、傅振伦、吴宗慈、李泰棻、瞿宣颖等祖述章学诚的观点。李泰棻《方志学》云:“在中央者谓之史,在地方者谓之志,故志即史。”甘鹏云《修志答问》提出:“一省通志即一省历史也,一县志乘即一县历史也。”今人持此论者亦较多。如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称:“方志是地方之史。”李宗邺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亦云:“地方志就是地方史。”方志学者中,也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如李玉成认为地方志即地方史,他说:“地理书、资料性著述、地方文献、行政管理学、百科全书,只是方志演变过程的不同阶段或不同侧面的表现,是方志易变的、不稳定的、次要的质;地方史才是方志比较深刻的、相对稳定的、主要的、根本的质,是方志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殊的本质。”[2]台湾学者黄纯青、林熊祥、宋晞等亦认为地方志即地方史。
关于“史志关系”的问题,清初的一些学者即在承认“志属史流”的前提下,注意到史、志之别。如程大夏在康熙《黎城县志·叙例》中说:“志与史不同,史兼褒诛,重垂诫也;而志记一地佳景奇迹,名人胜事,以彰一邑之盛。”乾隆《无锡县志例》亦曰:“史远而志近,史统而志专。”新方志编修工作大规模开展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过激烈的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史志无别”论。这种观点认为,志即史,史即志,史、志是同义词,称地方志为地方史也未尝不可,理由是:在内容上,地方志以记载过去的历史为主,这与地方史并无本质的差别;在体例上,地方志所采用的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源于古代史书;在方法上,地方志以纂辑史料为主,虽重记不重论,但不能改变其史的性质。二是“同中有异”论。这种观点认为,志与史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地方志属于历史范畴,但又不等同于历史。
地方志属于历史学科的观点,在历代目录学上也有反映,尤其在明代,许多私家图书目录把地方志区别于地理书而另列入史部。如嘉靖年间朱睦㮮在《万卷堂艺文志》中将“地志”列为史部的一个独立门类后,万历时连江陈第的《世善堂藏书目录》史部有“方州各志”类,著录志书104种。明末清初,常熟钱谦益撰《绛云楼书目》,亦于史部设“地志类”。康熙中之昆山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光绪间杭州汪少洪、汪蓉坨《振绮堂书目》等,也在史部为方志立了专门类别。这不仅表明方志在学术地位上的变化与提高,反映了历代藏书家对于地方志书性质的看法,而且在方志目录学上为后世编目开了一个好头。
三 史地两性说
民国时期,随着地理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些学者提出,方志既是地理书,又是历史书,“史地兼有”。当代学者中也不乏赞同此论者。
朱希和在为《新河县志》所作序中指出:“作县志之法,能兼得今世历史、地理二学之所长,乃为善志。”朱士嘉认为,方志“盖无异一有组织之地方历史与人文地理也。书之关系一方者,统称志”[3]。黎锦熙认为,“折中之论,则谓志之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惟是兼而未合,混而未融”,进而提出了“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等论断[4]。于乃仁亦称:“方志者,以地方为单位之历史与人文地理也。”[5]民国方志界,以黎锦熙持此说为最著名。故黄苇等著《方志学》称:“‘志兼史地’说的发明,是民国方志学的一大贡献。”该书亦持此说,称:“方志不仅以地域为记述空间,具有地理性,而且以一定时间为限,具有明显的历史性,方志已融合史、地两种著作的特点,不能单以任何一种视之。”台湾学者杜学知也认为,“黎劭西先生更为‘方志者,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理化’,折中于新旧两派之间,融会史地的两种特性,最能不烦言而尽方志性质的底蕴”[6]。此外,李宗侗、毛一波等台湾学者亦持此说。
持“史地两性”论者认为,方志以地域为记述空间,故具有地理性,又以一定时间为限,故亦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地方志兼容了地理、历史两种学科的特点。反对意见则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折中论,并未提出有价值的见解。也有观点认为,此论虽是折中之论,却给后人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启示,这就是:“如同骡子亦驴亦马,因而也就非驴非马而另称骡子一样,方志既然亦史亦地,那就必然非史非地,而另有性质待考。”[7]
四 “政书”、“辅治之书”说
视方志为“政书”、“辅治之书”,历代颇不乏人。明人林魁云:“志者,言治之书也。夫纪成垂远,为治计也。”雍澜亦云:“志也者,经治之书也。”清代,李奉翰称:“志者,固辅治之书也。”黄时沛亦曰:“志者,政事之书也。”当代学者于希贤也明确提出了“方志为政书”的主张,认为方志无论今古,内容都“是行政管理知识的总结”,作用都是“为资政决策提供基本知识”,为当时的行政管理服务,所以“它和行政管理一样是一门政治性、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8]此外,也有学者从方志“从春秋战国时期发端以来,就被历代统治者作为管理国家、加强政权建设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立论,认为地方志是“官书”,其主要特性是“官修性”。[9]
反对意见认为,方志为政书、官书、辅治之书的观点是从方志的功能作用着眼的,这本身就违背了实质性定义的规则;具有资治功能的著作极多,如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几乎无一不具备资治功能,如果仅从资治功能立论,这些学科的著作皆可名之为“资治之书”或“政书”,那么,方志的特殊性何在呢?[10]
五 “信息书”说
刘伯伦提出,地方志为“一方信息全书”。他说:“方志的科学属性,向来存在历史学派和地理学派之争。我们今天来看,它是以地为坐标、以史为线条专门以存储和传输地方信息为能事的一门科学。”这一点,若从编修地方志的过程来看,方志与信息的关系就更加明显:“搜集资料便是对信息的收集;审核资料继而进行条理、系统、详略得当的编写,便是对信息的处理。最后出版成书,流行于世,又何尝不是对信息的存储和传输。”由此,他提出:“作为一方信息全书的地方志就应理直气壮地从历史学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方信息学。”[11]李汝舟也认为:“方志,是一定区域一定时间断限内的信息集成。”[12]
反对意见认为,信息和信息学与方志和方志学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它们记述内容不同,编纂体例不同,研究对象不同,把它们混同或等同起来,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13]不能因为方志中储积了许多历史信息,便把它说成是“信息总库”,“信息是否可作为既不完全是物质的又不完是精神的特殊形态而存在?对于这一本质性的问题,科学界尚未盖棺定论,方志学界又怎么能够借用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来定义方志的性质呢?……把方志等同于信息,把方志学等同信息论,把方志定性为‘信息全书’或‘信息总库’,我们无法看出方志的本质特征。” [14]
六 “资料性著述”说
这种观点在《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施行之前,盛行于方志界。1986年12月,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编出来的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此后,持此论者众多,逐渐成为方志界的共识。如刘柏修说:“地方志是记载一定区域自然、人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15]宋永平说:“方志是全面系统记述一方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16]梁滨久说地方志“是记述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17]。魏桥说:“地方志是综合记述一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全面情况的资料性著述。”[18]张景孔说,地方志“是真实记载一定行政区划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性著述”[19]。欧阳发说:“地方志是以行政区划为范围,以一定之体例,记载一方从自然到社会各个方面的现状与历史的资料性著述。”[20]诸家说法,大同小异,都肯定了方志的资料性著述的本质属性,只是中心词前的修饰词语强调的方面有所不同。台湾学者郑喜夫也有相似的表述,他说:“地方志书者,系记载一定行政区域范围内有关自然及社会各种现象之正确历史与现况之资料性独特书体。”[21]
持此论者认为,方志的价值就在于它所提供的有关一地(指区域性综合性志书而言)自然、社会、人文的全面、系统、客观的资料。资料性是志书最基本属性,它决定和影响志书的其他属性。志书的资料是在一定思想观点统率下的资料,能够反映所记事物的规律和本质面貌,显示出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它又带有著述性,是资料性和著述性的统一体。
反对意见认为:“这一表述也是不周延和含糊不清的,因为它没有说明这种资料书或资料性著述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书,许多学科或部门都有自己的资料书或资料性著述,岂止方志有此特性?”[22]编纂方志离不开资料,但若仅视方志为资料性著述(实际上等同于资料),必将降低方志的学术地位和价值。
七 “地情书”说
较早提出此说的是刘辰,首先见于其《方志性质与编研实践》一文,以后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讨论。[23]他认为,地方志有“地方”和“情况”两个重要的规定,其体例随着地情变化而不断变化,新志编纂要因应时代需要,不断探索科学记载地情的新形式、新方法。陆天虹也认为地方志是国情书、地情书,他说:“地方志是记述特殊的、局部的、具体的地区历史资料的,是国情的分区记述。”[24]刘以发认为,“方志是分类编著的地情书”,并说这一定义:第一,可以囊括方志的全部内容;第二,可以涵盖方志收载的各种地域范围;第三,可以包举方志的所有著述形式;第四,可以为繁荣方志编著提供理论依据。[25]何萍则说:“方志是官修的地情书。”[26]
反对观点认为,不能因为方志可以为判定地方发展战略提供情况依据,便把它说成是“地情之书”。“地情书”的定义,“回避了方志性质特殊的‘质的区别’,只承认普遍性,迎合了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没有揭示矛盾的特殊性”。[27]若用“地情书”给地方志下一个古今通用的性质定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这些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形态(或叫载体)都是方志,那么它们之间质的差别又在哪里呢?”[28]
八 “百科全书”说
此说最早见于1980年。该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中国地方史研究会筹备会上,朱士嘉、朱文尧、梁寒冰、梅关桦等提出,地方志是“百科全书”,《中国地方史志通讯》总结道:“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载某一地方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和现状的百科全书。”之后,董一博也提出:“地方志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29]此论强调了方志兼记自然和社会、记事门类众多的“百科”特点。
反对者认为,视地方志为“百科全书”是欠妥的,因为百科全书“是类书性质,可多可少,可分可合,以传播知识为主,而地方志则是以特定地区的现实事物为主”[30]。地方志和百科全书虽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其一,百科全书以介绍文化科学知识为主,地方志则不是简单地介绍文化科学知识,而是要系统地反映一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兴衰起伏的客观发展过程。其二,地方志有自己的编写体式和义例,说地方志是一地之百科全书,只是一种比喻。”[31]也有论者从著作载体、编纂目的、编撰结构、记述事物的角度和要求等方面,分析了地方志与百科全书的不同,强调把地方志等同于百科全书,对编纂新方志是十分有害的。[32]
九 “一方古今总览”说
此说大致源于章学诚“修志必须统合古今”的观点。民国时期,于乃仁明确提出了“方志为一方总览”[33]的观点。黄苇也提出:“方志乃一方古今总览。”[34]并在其《方志学》一书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论定‘方志为一方古今总览’,不仅概括了方志的时代性、地方性、统合古今性,而且体现了方志的无所不载性、资料性、可靠性。”[35]此论着眼于方志记述一方历史和现状之全貌的特点,强调了方志在空间上的地域性、时间上的统括性、内容上的全面性等独特性。
反对意见认为,这一定义词义含混,内涵不确定,逻辑上也不严密。“古今”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用以概括记述有上下时限的地方志是不够准确的。首轮新编地方志因记述的许多事物需要追溯至清代及清之前,称“古今总览”尚可;正全面开展的第二轮修志,主要记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如仍称为“古今总览”,就欠妥当了。“总览”用于概括方志记述的内容,其内涵也显得笼统。[36]
十 “资料书”说
1961年,卢中岳所著《地方志史话》一文针对方志编纂历来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订,资料性很强的特点,提出:“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区有关地理历史方面的历史性资料。”[37]仓修良在《章学诚与方志学》一文中也指出:“方志是以地区为中心,记载某一地区有关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之历史性资料。”1986年,胡乔木提出,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此论一经他提出,影响较大。但有学者认为,胡乔木的说法和“资料性著述”的提法是一致的,并不矛盾,因为他在同一讲话中也说地方志是“著作”。他之所以强调地方志是“资料书”,主要是针对当时修志工作中存在的“政治化”倾向而言的。[38]也有人认为诸说中,胡乔木关于地方志的论断最正确、最中肯,肯定地方志是“依照传统,由地方行政部门(或由其组织)编纂,全面、系统记述地情的资料书”,而地方志是“著述”的观点,“动摇了地方志的根本,造成了认识混乱,对实践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当然,“如果‘著述’是指不能照搬原始资料,需要做好取舍、详略、考证等编辑工作,编者要有精辟的见解,那么说方志是一种‘著述’也未尝不可”。[39]
反对意见认为,此说突出强调了方志的主要特征是资料性,曾对新方志编纂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但“定位低”,“只谈到方志的作用,实际上并未接触方志本质”,“不能因为方志能够提供资料就将方志定性为资料,资料性不为方志所独有”。[40]相关意见认为,历史资料可以是各种原始资料的原件辑存,也可以是经过编纂者的考订、取舍、编次,以编纂者的语言加以表述的著作。历史性资料说忽略了方志的著述性,因而不是对方志性质的完整概括。
除了上述列举的几种主要定义外,关于方志性质的定义还有不少,如“是全面记载一定行政区划的自然、社会、人文等历史和现状的综合著述”;“是一种记载某一地区历史、地理、社会风俗、经济文化等方面综合性著作”;“是以地域为单位(主要是行政区划),按一定体例,综合记载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方面的书籍”;“是记述一定地域内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科学的、资料性的、独特的文字载体”;“是一种学术综合性社会科学著述”;“是一项以交流地情信息为根基的学术文化事业”,“广义方志是指包括从方志实践到方志理论或从方志编纂到方志接受全过程的整个方志事业”;是“认识并记述地情的资料性著述”,等等。定义的不同,与研究者的方法论、对方志形成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的认识、逻辑思维方式以及文字表达方法等因素密切相关。
在当前情况下,要给“方志”下一个相对精确的定义,最基本的依据仍是修志实践,同时,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地方志的性质,必须着眼于地方志的本质,注意定义范畴的时间性与适应面,明确几个关系:第一,在用词上,不要在一些同义词上咬文嚼字,要在关键性的词汇上下工夫;第二,在简称与全称上,要注意其相关关系及在不同场合的不同使用方法;第三,在外延与内涵上,要搞清楚不同表述的不同外延与内涵;第四,在狭义与广义上,要明确使用时因语言环境不同具有狭义与广义之区别;第五,可以分为工作与学术两个层面,应用于工作上的定义应有较为统一的表述,要考虑有利于地方志工作的开展,并有较广的适应面;而学术上的定义应允许百家争鸣,可有多种表述方式与诠释;第六,在通用与专用上,要分清词汇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分别不同场合予以使用。本着这样的原则,在起草《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过程中,曾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方志性质问题,根据讨论意见,确定地方志的定义表述至少应该包括这样一些核心要素,即:“地方志是记录特定区域自然、社会和人文的历史、现状的文献。”[41]此后,又不断对这一定义进行补充、完善。最终,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地方志的内涵为“资料性文献”,外延则包括志书(包括各级各类综合志书和专门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地方志工作条例》把专门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纳入地方志工作的管理范围,这既是对199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中已有规定的突破,体现了“大方志”的观念,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地方志工作的领域,同时又反映了地方志工作的实际。
这个定义,实际上是综合上述各种观点,对方志界多年来关于方志性质问题讨论成果所作的一个归纳总结。此定义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要素。
第一,空间——“本行政区域”。古代指省、府、州、郡、县、乡、镇、里、村等,现代指省、市、区、县、乡、镇、村等。
第二,时间——“历史与现状”。任何志书都明确规定自己所记述的时间范围,即上限、下限,志书要记述的就是这个时间断限内“本行政区域”的“历史与现状”。
第三,内容——“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
第四,形式——“全面系统”。地方志体例的最大特点是分门别类(通常说横分门类),纵述史实,事以类从,类为一志,这实际上就是“全面系统”要求的具体体现。
第五,性质——“资料性文献”。一方面,资料是志书的生命,志书的价值主要在于资料,因此志书是资料性的书。另一方面,志书的资料又不同于原始档案资料,它是经过精心筛选、综合、归纳、提炼之后,按照志书体例要求进行科学分类,然后用编者自己的语言客观地、规范地表达出来,具有文献价值的资料性著述。按照《辞海》对“文献”的解释,文献原指典籍与宿贤,后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如历史文献;亦指与某一学科有关的重要图书资料,如医学文献。今为记录有关知识的一切载体的统称,即用文字、图像、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以记录人类知识的各种载体,如纸张、胶片、磁带、磁盘、光盘等。据此,将方志定位为“资料性文献”,是妥当的。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定义更多是从工作层面提出来的。至于学术层面的争鸣,是可以而且应该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的。
注释:
[1] 转引自唐祖培《新方志学》“志体”,台北华国出版社,1995年。
[2] 李玉成:《方志的本质》,载《广西地方志》1997年第1期。
[3] 朱士嘉:《方志之名称与种类》,载《禹贡》1934年第1卷第2期。
[4] 黎锦熙:《方志今议》,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
[5] 于乃仁:《方志学述略》,载《建国学术》1942年创刊号。
[6] 杜学知:《台省通志纳目商榷》,载台湾《中国内政》第2卷第2~4期。
[7] 刘柏修、刘斌主编《当代方志概论》,方志出版社,1997年。
[8] 于希贤:《试论中国方志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载《云南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1期。
[9] 何萍:《也谈地方志是什么书》,载《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5期。
[10] 参见刘以发:《方志定义论》,载《云南史志》1998年第1期。
[11] 刘伯伦:《方志与信息》,载《山西地方志》1985年第4期。
[12] 李汝舟:《方志学与信息学》,载《湖北方志通讯》1985年第3期。
[13]参见穆恒洲:《方志性质再认识》,载《方志研究》1989年第6期。
[14]刘以发:《方志定义论》,载《云南史志》1998年第1期。
[15]刘柏修:《人口部类应该与自然、社会等量齐观》,载《江西地方志》1988年第2期。
[16] 宋永平:《试谈方志的宏观与微观论述》,载《福建史志》1992年第4期。
[17] 梁滨久:《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石》,载《方志研究》1992年第5期。
[18] 魏桥:《毛泽东与地方志》,载《中国地方志》1993年第5期。
[19] 张景孔:《新编志书的观点及其表述》,载《陕西地方志》1993年第5~6期。
[20] 欧阳发:《关于方志及方志工作的思考》,载欧阳发、何静恒主编《方志研究与评论》,方志出版社,1995年。
[21] 郑喜夫:《〈地方志书纂修方法〉之探讨》,载《台湾文献》第53卷第1期。
[22] 黄德发:《史志关系辨析》,载《广东史志》1992年第1期。
[23] 参见刘辰:《方志性质与编研实践》,载《史志文萃》1988年第6期。
[24] 陆天虹:《地情书与官书两议》,载《江苏地方志》1990年第3期。
[25] 参见刘以发:《方志定义论》,载《云南史志》1998年第1期。
[26] 何萍:《也谈地方志是什么书——兼同资料书说商榷》,载《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5期。
[27] 王晖:《论方志性质》,载《中国地方志》1990年第1期。
[28] 张侠:《“地情书”说质疑》,载《方志天地》1990年第3期。
[29] 董一博:《董一博方志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30] 彭静中:《中国方志简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
[31] 黄德发:《史志关系辨析》,载《广东史志》1992年第1期。
[32] 参见王矩:《浅议地方志与百科全书的区别》,载《广西地方志》1994年第5期。
[33]于乃仁:《方志学述略》,载《建国学术》1942年创刊号。
[34]黄苇:《章学诚方志理论研究》,载《方志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35]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
[36]参见甄人:《一代志坛: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与实践》,方志出版社,2002年。
[37] 卢中岳:《地方志史话》,载《人民日报》1961年11月19日。
[38] 参见梁滨久:《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载《河洛史志》1991年第4期。
[39]丁一:《谈地方志的几个基本问题》,载《广西地方志》1999年第2期。
[40]孟庆斌:《方志资料性浅议》,载《中国地方志》2001年第1~2期。
[41]《方志性质研讨会纪要》,载《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期。
(编校:闵洁 审核:张晶萍 排版:刘云锋)
- 2025-04-17
- 2025年保密公益宣传片《指尖的守护》
- 2025-04-17
- 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 2025-04-15
- 宁波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宁波简志》
- 2025-04-15
- 内蒙古赤峰市扎实推进苏木乡镇(街道)志编修工作
- 2025-04-14
- 跨越时空的文化寻根之旅 国家方志馆粤港澳大湾区分馆受热捧
导航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