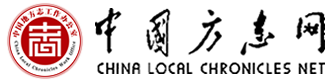地方志或称方志,其编修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方志作为带有地方行政区域特色的地方性著作,究竟起源于何时,其渊薮何在?这不仅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迄今尚无定论的课题。有关方志起源问题,有的远溯殷商,有的则云晚至宋代,据有学者统计,至少有17种说法[1]。诸家之说,择其要者大致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一 方志起源于《周官》说
《周官》即《周礼》,是一部记述周代官制的著作。方志起源于《周官》之说,最早见于宋司马光《河南志·序》,此序中说:“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也。唐丽正殿直学士韦述为《两京记》。近故龙图阁直学士宋君敏求,字次道,演之为《河南》《长安》志。”[2]司马光在这段论述中,从北宋宋敏求纂修的《河南志》和《长安志》出发,上溯到唐韦述所撰《两京记》,然后将其源头直追至周官的职方、土训和诵训,认为方志渊源就在于此。

司马光主张方志导源于周官职方、土训、诵训的理由,推究起来,首先在于,据《周官》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3]《周官》的这段记载及其以下的解释表明,职方氏执掌天下之图和地,并按扬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这九州之国,辨明各地的山川、湖泊、薮泽、人民、物产、财用等,而这些方面正是后世方志所多载。所以,在周官职方氏的这类职掌中已露后世方志之端倪,从而可以说是其渊源所在。其次,周官“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4]。据东汉郑玄注称:“道,说也,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荆、扬地宜稻,幽、并地宜麻。”[5]这可看作职方的补充,也同后世方志有渊源。此外,《周官》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6]郑玄注称:“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若鲁有大庭氏库、殽之二陵。”[7]这类古迹遗事也是后世方志所多载,从中亦可察知其间存在渊源关系。所以,司马光云,后世学者仿周官职方、土训、诵训,为书以述地理。
二 方志起源于古史说
这一说法直接提出后世郡县志书便是古代诸侯国史。宋代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言:“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
明代,视史、志一体的看法已极为普遍。明代万历《河东运司志》蒋春芳序称:“夫志,史乘之流也。”嘉靖《河间府志·序》中说:“古有列国之史,而今有一方之志,是虽名谓有殊,而核名实以记时事者,其义同也。”这就明显地将古代“列国之史”与当今之“一方之志”完全等同起来了。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更是着力强调史志同源,他说:“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8],一时成为主流,一直较其他诸说流行,影响至今。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可见这一说法影响之大。方志学家李泰棻在其《方志学》一书中也称:“在中央者谓之史,在地方者谓之志,故志即史。如某省志即某省史,而某县志亦即某县史。”直接地将地方志与地方史视为同体,别无二致。即使今日,一些人仍习惯将地方志同地方史等同起来,不分界垒。
还有一些与上述观点相近的说法,认为方志源于古史书,或推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或起自《越绝书》《吴越春秋》,或源于《华阳国志》。虽上溯的年代有异,所指的源头不同,但认为方志源于古史书的见解却是相同的。例如章学诚即认为“郡县志乘即封建列国史官之遗”,即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演变而来。
当代有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的撰写虽曾盛极一时,但遗憾的是这些书籍未能流传下来,以现存的《春秋》经传考之,无论在体裁,还是内容上,同后世的方志大不相同。以现存往往被推为方志源头之一的《华阳国志》而言,也多偏重于地理,同后世方志尚有较大的距离。至于《越绝书》《吴越春秋》二书同后世方志相比,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更为明显了。客观而论,史学对历代方志编纂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与影响,史学各种书籍的体裁、形式的产生与发展,为方志的修纂提供了借鉴的体例和丰富的营养,于今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但若简单地据此将史志完全等同为一体,而无视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其他学科对方志的影响,就难免失之片面了。[9]
也有学者认为,方志源于古史说所持理论,所讲者亦大多着眼于古代各诸侯国,其领域很小,有如后世郡县之规模。很少从所记内容和著作体例考虑,实际上是只看形式而忽略了实质。古诸侯国领土虽小,但它的性质与职能毕竟与后世之郡县不同,两者自不可同日而语。况且诸侯国史所载内容正如明代史学家王世贞所说“不过君卿大夫言动之一端”,不像方志所记内容那样丰富、广泛。再从体裁而言,诸侯国史大多为编年纪事之体,这是当时史体的主流,与后世方志体裁的多样性也全然不同,因此很难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渊源关系。虽然梁启超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无法自圆其说,而不得不承认“唯封建与郡县组织既殊,故体例靡得而援也”[10]。既然体例、内容并不相同,一定要强调两者有渊源关系,则实在是过于牵强。[11]
三 方志起源于《禹贡》说
当代有学者认为,综览古今有关方志论述,虽主张方志导源于《禹贡》者较少,居于次要地位,但因此观点历来为人广泛传述,因此同样值得重视。首先,从体例来考察,后世纂修的许多方志,特别是全国性的区域志,不少是昉自《禹贡》的。例如,唐李吉甫纂《元和郡县图志》,就是依《禹贡》别九州之例,将天下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及陇右等十道来进行载述的。[12]又如,宋王存纂《元丰九域志》,也依《禹贡》别九州之例,按宋制将天下分为四京及京东、京西、两浙、江南、荆湖、梓州、夔州、福建、广南诸路等,而确立其全书结构。[13]这都说明后世方志在体例方面同《禹贡》存在着源流关系。其次,后世有些方志的若干载述内容也昉自《禹贡》。例如,《元丰九域志》在确定了分天下为四京及京东、京西等诸路的体例结构后,又于各路之下分别条列本路地理、户口、土贡及属县等。这在内容叙述方面与《禹贡》诸州记载略同。此外,元人朱思本在所撰《九域志·自序》中叙述其志所本时,还曾明确自称是以《禹贡》为准。
四 方志起源于《山海经》说
探索方志源流,所以要述及《山海经》,首先是因为有些旧方志叙述纂修缘起时,每每提及此书。宋元丰间,王存纂《九域志》,据《玉海》载称:至“绍圣四年九月十七日,兵部侍郎黄裳言:‘今《九域志》所载甚略,愿诏职方取四方郡县山川、民俗、物产、古迹之类,辑为一书,补缀遗缺。’诏:‘秘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14]黄裳所要辑补的即是后来成书之《绍圣九域志补遗》。此志虽纂者不详,且已亡佚,但从“诏:‘秘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来看,当是以《山海经》为主要源本。

《禹贡》记物产而不及风俗,然《山海经》所述,既有风土、人情,又涉人物、世系。这些不仅补《禹贡》之无,而且正同后世方志风俗、人物门类吻合。此外,后世方志多有祠庙、碑碣、仙事、异闻等记录,考之《山海经》,亦有祭祀、巫医、神祇、怪异等载述。由此亦可见方志某些内容有来源于《山海经》之痕迹。所以,若谓《山海经》亦是后世方志源头之一,确无不可。[15]
应当指出,后世方志与《山海经》相比,无论内容还是体例结构,毕竟在多方面大异其趣。就可信程度来考察,方志虽也记载神怪异闻,但属末节,主要部分是纪实,因而较为可信;而《山海经》,虽经后人考证确定,知其中载有较为真实的地理和物产材料,然而大部分仍属神话传说,难以凭信,因而二者也互异。所以,《山海经》不仅谈不上是方志,而且即使确定它同方志有渊源,也只能说是次要源头之一。[16]
五 方志起源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说
关于方志的起源,还有多家提及《越绝书》《吴越春秋》以及《华阳国志》等。自清人毕沅在乾隆《醴泉县志·序》中提出“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之说后,后来许多方志学家遂相沿其说。当前方志学界亦有人把它称为现存之最早方志。

后世言及方志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之间关系者,有以下诸家:
清洪亮吉云:“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17]清廖寅曰:“唐以前方志存者甚少,惟《三辅黄图》及晋常璩《华阳国志》最古。”[18]近人傅振伦称:“《越绝》《华阳》二书,皆为方志之类,率述一地偏霸历史沿革,及其掌故、风土、人物。自古志逸,而此遂为地方志之所自昉。”[19]李泰棻言:“志即史也。故如《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未能传世之百二十国宝书等,皆可称为方志。然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20]范文澜亦认为:“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典故,开方志之先例。”[21]
当代学者认为,诸家之说,都只说明《越绝书》《吴越春秋》和《华阳国志》,或为方志之始,或乃最古之方志,或系方志所自昉或开方志之先例,并未涉及方志源头问题,故不能据以将此三书看作方志渊源所自。[22]
六 方志多源说
除方志起源于某部典籍之外,还有方志多源说。这种观点认为,《周官》《禹贡》和《山海经》都同方志有渊源关系,其中的某些部分均是方志的源头。至于《越绝书》及《华阳国志》,则已是方志的发端或雏形。[23]元代张铉在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中言:“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记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四库全书总目》则总结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各家所言虽侧重不尽相同,但是大都关注方志多源。
当代有学者认为,除《周官》《禹贡》和《山海经》外,从有关古籍和另外一些记载来考察,尚可觅得方志的其他一些源头。《大元大一统志·序》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来尚矣。”[24]《九丘》成书甚早,在《左传》以前,即已流传,其内容又涉及“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故亦属地志之类,而且后世修志者在探索方志渊源时,已语及此书。所以,《九丘》亦可列作方志源头之一。后世方志同古舆图也有渊源关系。清人毕沅考证:“《山海经·五藏山经》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图。”[25]他又说:“《山海经》有古图。”[26]此说如确,则古《山海经》也是地图,至少是以图为主,文字不过是附图的说明,后经演变,图渐亡佚,而存说明,乃成为后来传世的《山海经》。近人王以中更进而据此认为,《山海经》是中国最古地图之残迹,并且断定今本《山海经》是古《山海经》亡图而残存的文字说明,而这类文字说明,又是后世方志的渊源所在。以上论述如果确能成立,则包括《山海经》在内的古舆图也应是方志的一个源头。总之,从上述多方面的种种情况看来,方志源头较多,不仅有《周官》《禹贡》《山海经》,还有《九丘》之书和古舆图等等。这还只是就已知的情况而言,如果进一步广泛深入考察,或者还可找到如民间传说等一类的来源。
持此观点者进一步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处于萌芽时期的志书同古史书、古地理书、古地图之间,并不是区分得很清楚,也很难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方志从萌生之期起,就从其他众多的相关学科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按照人们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地充实、完善自己,而逐渐演进成现今这种形式的志书。另一方面,其他与方志亲缘关系较近的相关学科也按照自身的轨道而繁衍成各自的学科体系,并反过来又为方志学科理论和修志实践提供营养和借鉴。因此,方志起源的多源性和源远性是中国方志起源的两个显著和基本的特征。[27]
七 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探索方志起源不能离开时代背景,即方志是在需要及可能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任何一种著作体裁,应当说都是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方志自然也不例外。方志的名称,较早时候,史家多称为“郡书”“郡国之书”“郡国地志”等,这就说明,它是记载以地方行政区划郡县为范围的一种著作。后来的发展,也正是沿着这样的方向,所以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动,就有府志、州志这一类名称。众所周知,郡县制度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才在全国确立推行的。既然如此,那么在郡县制度尚未确立之前,自然就不可能产生反映这种制度的著作。因此,方志这一著作形式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首先,战国时期历史观由重天命敬鬼神向重人事的变化,促使人物传记的产生,《史记》的诞生直接推动着人物传记的发展。人物传记乃是方志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种人物传到司马迁著作《史记》时才创立,先秦史书中虽叙述了各种不同人物,但作为人物传的形式当时并没有产生。《史记》的诞生在我国史学史上和文学史上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它的影响下,刘向首先写出了独立的传记著作《列女传》。此后,脱离正史,专写人物传记的风气从而逐渐盛行起来。特别是到了东汉、三国以后,更是非常发达,并出现了分类传记,如《高士传》《高僧传》《逸士传》等,分地域的传记,如《襄阳耆旧记》《会稽先贤传》《汝南先贤传》等。这就为方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些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与专记一方风土的地理著作相会合,便产生了最早的方志——地记。
其次,两汉魏晋的选举制度促使着人物传记的盛行。早在西汉初年,封建统治者为了选拔官吏,就已采取了由郡国举荐贤良方正的措施。到了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逐渐形成汉代选拔官吏的察举制度。后来这种察举制度一般都以郡国名士主持的乡闾评议为主要根据,并形成一种社会风气。魏晋以来,各朝则又相继实行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实际上是汉代察举制的发展。无论察举制还是九品中正制,都是封建统治者用以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被选拔的士人都要进行一番评论。既然政治上盛行对人物的评论,就必然直接影响到史学上也注重褒贬人物的风气。
再次,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势力的强大是产生地记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在西汉时期,许多豪族地主便大肆兼并土地,横行乡里。到了西汉后期,许多豪族地主占有土地以后,便采用庄园的经营方式,东汉开始以后,这种庄园形式便逐渐在各地建立起来。这些豪族地主,当他们经济力量非常雄厚以后,便进而要取得政治权力以保持其既得的经济地位。于是他们便利用察举选官这一制度,相互勾结,互相标榜,相互推荐亲属故旧,这样势必要制造舆论,需要地方性的著作来为其服务,“地记”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时而生。特别是到了“选举而论族姓阀阅”“贡荐则必阀阅为前”的时候,宣扬显赫的家世、打出祖先的旗号,就更加显得重要了。所以各地都有所谓“先贤传”“耆旧记”“风俗传”之类的著作出现。开始时也许就是人物传记,但不久便与专记一方风土的地理相会合,这便是最早的方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方志的雏形——地记。当然,这种“地记”,有的是称“某地记”,有的则仍旧称传,如《南阳风俗传》《关东风俗传》等,自然不能把它们看作单纯的人物传记。[28]
由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与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相汇合而形成了地记,这就是方志发展的早期形式。当然,在最初的时候,人们对于名称并不大注意,因此有的称志,有的称传,有的称记,有的称录,也有的称图经,名称并不统一。但从后来发展趋势看,称记者为多,称志者也不少,如《陈留志》《南中志》《豫章旧志》等,不过这种志,是与记的意思一样,就是记事的意思。看来形成“方志”这个专有名称,还是有一个相当的历史过程的。尽管当时出现的名称不一,但这种地记的内容,不外乎都有山脉河流、地理沿革、风土人情、人物传记等方面的内容。[29]
另有学者指出:方志之名始见于《周礼》。《周礼·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据郑氏解释,“志者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其实这些都是一国的史书,和后来的方志不尽相同,较为具体的,则是《后汉书·西域传》中所提出的“二汉方志”。当时不仅有方志名称,而且方志的著作也是相当的繁多了。现在传世的尚有《三辅黄图》和《三秦记》等,虽属辑本,但大体可见一斑。[30]
上述学者关于方志起源的论述虽不尽一致,但大体上主张方志起源于两汉或汉魏时期,并在否定方志起源于《周官》这一点上达成一致。
方志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释:
[1]参见刘纬毅:《中国地方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19~23页。
[2](北宋)司马光:《河南志·序》,《司马温公传家集》卷六十八。
[3]《夏官司马》下,《周礼》卷八。
[4]《地官司徒》下,《周礼》卷四。
[5]《地官司徒》下,《周礼·郑氏注》卷四。
[6]《地官司徒》下,《周礼》卷四。
[7]《地官司徒》下,《周礼·郑氏注》卷四。
[8]《文史通义》外篇一,《方志立三书议》。
[9]参见王德恒、许明辉、贾辉铭:《中国方志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1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3)。
[11]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25~26页。
[12]参见(唐)李吉甫纂《元和郡县图志》卷首,目录。
[13]参见(北宋)王存纂《元丰九域志》卷首,目录。
[14](南宋)王应麟辑《玉海》卷第十五,地理,元丰郡县志。
[15]参见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7页。
[16]参见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5~99页。
[17](清)洪亮吉:《新修澄城县志·序》,清乾隆《澄城县志》卷二十,序录十八。
[18](清)廖寅:《校刊〈华阳国志〉序》。
[19]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第十二章,《越绝书》与《华阳国志》。
[20]李泰棻:《方志学》第一章,概论。
[2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246页。
[22]参见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0~100页。
[23]参见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0~104页。
[24](元)许有壬:《大一统志·序》,《圭塘小稿》卷五,序。
[25](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山海经笺疏图说》。
[26](清)毕沅:《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山海经笺疏圈说》。
[27]参见王德恒、许明辉、贾辉铭:《中国方志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28]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31~44页。
[29]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44~52页。
[30]参见史念海、曹尔琴:《方志刍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页。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编校:谢捷 审核:张晶萍 排版:刘云锋)
- 2025-04-17
- 2025年保密公益宣传片《指尖的守护》
- 2025-04-17
- 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 2025-04-15
- 宁波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宁波简志》
- 2025-04-15
- 内蒙古赤峰市扎实推进苏木乡镇(街道)志编修工作
- 2025-04-14
- 跨越时空的文化寻根之旅 国家方志馆粤港澳大湾区分馆受热捧
导航展开